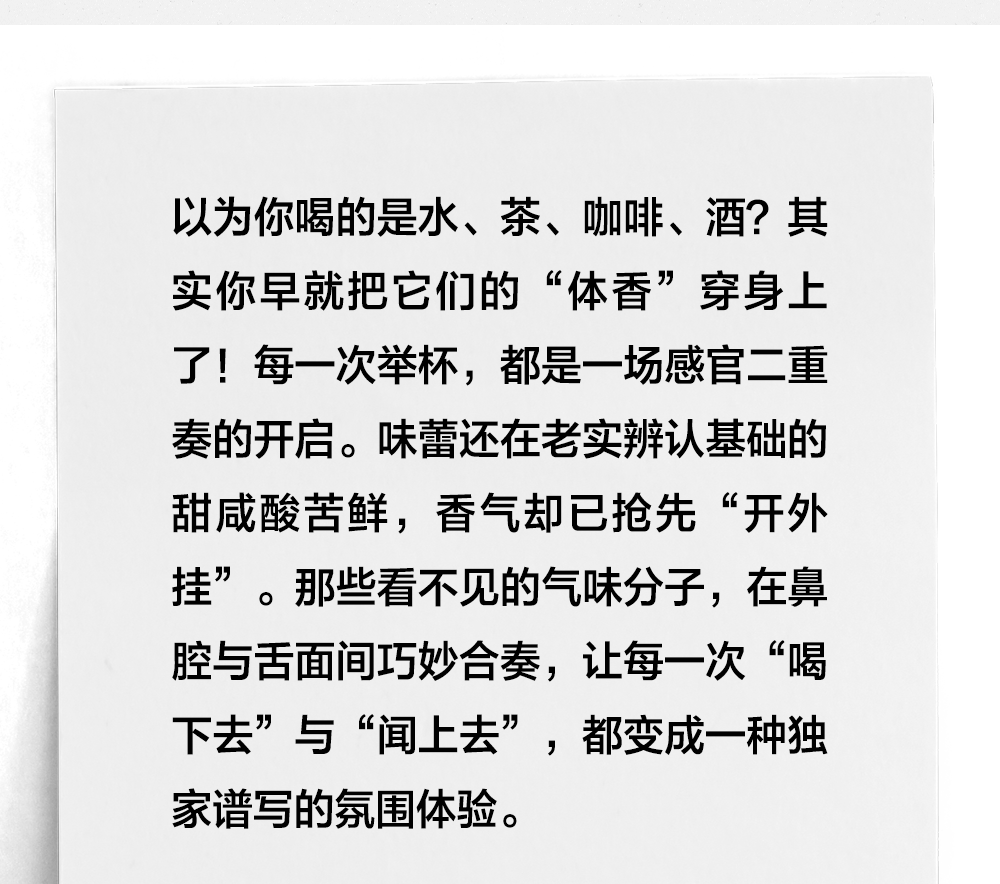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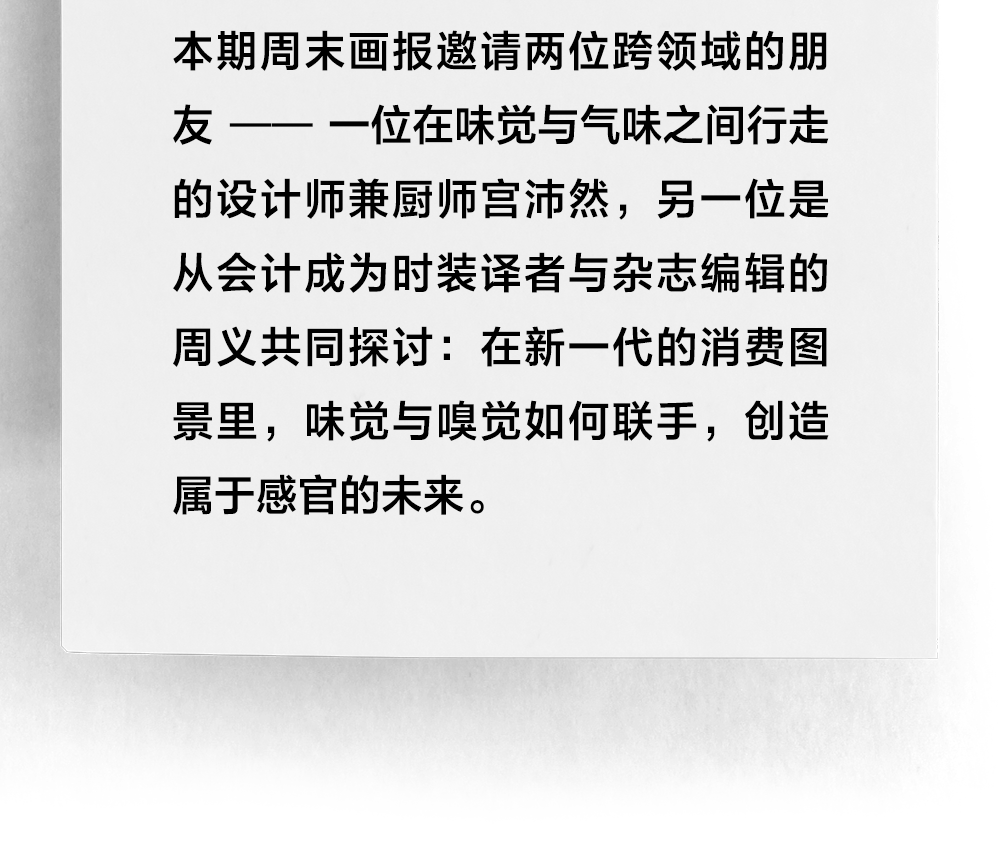

事实上,香水作为感知的延伸和弦,早已开始探究年轻一代如何用感官重塑消费的仪式感。法国Nez杂志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水从不是中性的,它是所有风味的第一面镜子。它本身近乎虚无,却因嗅觉的介入,幻化出千变万化的性格。”事实上,在味觉科学研究中,水从来都不是“风味上的空白”。当味蕾在接触纯净水时,会激活酸、苦、甜等基本味觉的受体,从而与嗅觉一同在脑海中制造出一种关于纯净的想象。冷泉里的矿物质感、山涧的湿润气息,甚至是自来水里的微弱金属,都会被味蕾与嗅觉受体放大成一帧帧不同的“风景”。

日本艺术家Kaoru Kan以水为主题的作品
三宅一生的L’Eau d’Issey一生之水,并非模仿水的气味,而是在传达水的“存在方式”。那是一种介于自然与意识之间的清澈,一种平衡与觉醒的精神气息。它的冷,不是拒人千里的疏离,而是如拂晓第一缕光线般的纯净与自省。莲花与水生调带来一种近乎透明的静谧,如水面上被风轻轻撩动的涟漪;铃兰与白玫瑰的气息仿佛空气中闪烁的湿度,让“清新”不再是一种表面的温度,而成为一种内在的秩序。在这份气息的深处,木质与麝香如“水的骨骼”,赋予它流动中的结构感。那不是温柔的包裹,而是极简的支撑——一种让清澈得以成立的深度。闻它时,你会明白,水并非无形。它有方向,有呼吸,有意志。它是万物的起点,也是感官归零的终点。当所有气味都褪去浮华之后,留下的,是那一瞬间的纯净。

Issey Miyake三宅一生一生之水女士淡香水

正如嗅觉学者Gordon M. Shepherd曾提到:“正是嗅觉赋予了味觉意义。”茶的滋味,则总是在“未言尽”的留白处被感知。当你在气息的流动中,看见了茶汤的颜色,听见了时间流淌的声音。轻抿一口,味蕾率先捕捉到的是苦与涩的框架,随即嗅觉将茶在烘焙与炒制过程中释放或吸收的花香、木香、甚至暖意填入其中,让茶的滋味开始丰富而饱满,变得更为完整。这种感官层面的补全,在感受香水时会得到完美的回响。

南宋刘松年《撵茶图》
在味觉的五线谱上,茶是一种极具留白的音符。它的滋味总是若隐若现、欲言又止——苦涩只是骨架,而香气,才是赋予它灵魂的部分。Le Labo的“黑茶29”并不是对“饮茶”过程的模拟,而是展现一种饮茶时“超我思想”。前几秒,月桂叶的微微清苦与绿意,像是茶叶边缘的青筋,带你进入那片还未完全打光的叶丛。香气渐深,木质感开始浮现——雪松、香根草与麝香交织,为这杯“茶”撑起骨骼。接着,烟草与干草在底层出现。茶香的边界在此被拓宽——你仿佛能闻见叶柄、能闻见枯草、能闻见烟雾与时间的痕迹。此刻,茶不再只是“入口即逝”的味觉,而有了体温与张力。这一刻,茶的精魂却在你鼻腔、你的意识里缓缓蔓延。它如一条无形的河流,从呼吸进入,再流入记忆深处。你无法用“甜”“苦”“涩”完整描述,因为这支香水里的“茶”在时间里活着——它有层次、有呼吸、有温度、有灰尘,有那些茶叶在风里颤动的声音。

从上至下
Louis Vuitton路易威登“茶瀑”香水
Le Labo勒莱柏经典香氛系列黑茶29

味觉的深度,不来自浓度,而来自嗅觉的延展。法国感官学者Hélène Delwiche曾在《Chemosensory Perception》上指出:若没有鼻后嗅觉,咖啡只会尝起来苦与酸,印证了咖啡的风味感知有强烈的“跨感官”效应。咖啡的力量则在于,它不是单一的饮品,而是一种味觉被嗅觉“修正”的典型案例。在《Food Quality and Preference》2008年的一项研究发现,即便实际糖分含量没有变化,咖啡的香气能显著提升人们对甜味的感知。这意味着,嗅觉不仅塑造了风味的复杂性,更在心理层面改变了我们对“苦”与“甜”的价值定义。舌根感受到的第一口的焦苦,总是被鼻腔里涌起的烘焙香气所平衡,那些隐藏在苦涩背后的焦糖、烟草甚至花香的感受和表达,懂得品味苦才真正懂得了生活的滋味。而为什么人类会迷恋“苦”的滋味?或许因为甜是与生俱来的渴望,而苦像一种逼近灵魂的暗香。茶、咖啡、威士忌、巧克力——这些“成人的味道”无一不是教会我们在苦里等待,在涩里寻找余韵。

土耳其艺术家Cansu Porsuk Rossi作品
香水对咖啡香气的借鉴,往往着眼于“生活的深度”。Tom Ford的Café Rose并不在意穿着者是悦己还是悦人。它像一段复杂关系的气味,花香的甜、咖啡的苦、香料的热,在这里并存。正如任何一段关系的节奏:前调刺激、心调缠绵、尾调安静得近乎冥想。初闻是黑咖啡的苦意,紧接着玫瑰浮现,那花香并非新鲜花束,而是被时间、烟与思绪烘烤过的玫瑰。那种不再追求表面的明亮与干净,而是允许香气里有沉积、有杂质、有回声。咖啡在这里的苦并不拒人,而是一种邀请,玫瑰的香气如光,在深处闪烁出人性的温度。并用香气讲述,生活的深度不是多,而是浓;不是快,而是慢……

从上至下
Tom Ford Beauty汤姆·福特咖啡玫瑰香水
Diptyque蒂普提克暖木之息大千之蕴淡香精

人们对同一款酒的评价,会因酒香被感知的方式不同而发生显著差异(Shepherd, Neuroenology, 2017)。这意味着,喝酒不仅仅是“尝味道”,而是一次嗅觉与味觉交织的深度感官体验。虽然酒的味道,总是浓烈到无法被忽视。但酒的本质,与其说是味觉,不如说是联觉的高级幻术。以茅台为例:一开瓶,曲香与酯香便扑面而来,像是热烈的火焰点燃味蕾。入口时,辛爽、绵柔、甜苦交错,却在呼吸间被那股特殊的“醇香”统领。这正是因为茅台独特的风味源自多种挥发性化合物的整合,它们通过鼻后嗅觉路径抵达大脑感知风味的区域,远远超越了舌头的基本味觉分类。

美国艺术家Micheal McGregor作品
Penhaligon’s 潘海利根的Juniper Sling杜松司令淡香水像被一杯冷调杜松子酒迅速点燃。那种酒杯边缘带冰霜的触感仿佛在鼻腔边滑过,清爽与刺激同时诱动神经。进入中调,香气像夜色刚落下的微醺派对:黑胡椒与肉豆蔻的辛香如香槟里的气泡在鼻底跳跃,皮革调与鸢尾的柔滑调和其中,像绅士礼服的领口,既有结构也有张力。香根草和香木调最后出现,如同夜宴的尾声余温,像夜色下酒杯边桌布残留的轻香。整体酒意在香气里流淌,让人既在夜里,又在光里。

Penhaligon's潘海利根杜松司令淡香水
如今,Z世代不再满足于“喝到”或“闻到”,他们要的是“完整地感受到”:跨越感官的生活方式。无论是手边一杯冒着热气的黑咖啡,还是瓶中一抹带着疏离感的白茶香水,抑或餐桌上那杯充满文化张力的茅台,感官的叠加都在塑造着一种新的价值观。水、茶、咖啡与酒,这四种当代人最熟悉、最基础的味觉线索并行于生活里,而当我们把生活里的一饮一食皆当成一种体验,会发现味觉只是感受签到的入口,嗅觉才是体验人生滋味的隐形指挥。


从伦敦到大理,从发酵食物到茶与香氛,宫沛然的创作始终围绕“气”的流动——探索人、自然与时间的关系。
中国人常常说“气”。我们说一个人有灵气、一道菜有烟火气、一件设计有气韵。你如何理解“气”?
“气”是一种生命力的流动,是一种真实的状态,任何事物的有气无需专业“眼光”才能感受到。好的气息浑然天成,让人觉得自然、通透、没有刻意的东西。说一道菜有烟火气,一个设计有灵气也都是在说一件事就是“生命此刻在场”。
我一直觉得,去理解“气”,其实是去理解“整体”。那是东方文化里最微妙也最本质的部分。当你只谈论其中某一个部分——比如味道、香气、手艺,你就失去了对整体的感知。真正的“气”,是这些要素在当下瞬间达成的和谐。它是一种流动的平衡。
当你在泡茶或设计香氛时,你会感知到什么?那种感受能否被传递?
我最在意的是“当下的氛围”。这种感受跟场景有关,一个人泡茶或品香时,更多的是向内的感受,甚至神游;和人群一起时,茶和香也会成为媒介,形成场域, 使人放松交流。我觉得这种感受是能被传递的,但不是靠表达。
我曾在一次关于“气味晚宴”的讲座中听到:主厨会让客人先闻一种气味,再根据气味去提炼菜肴的元素。这件事让我特别震撼——因为气味真的能成为一种艺术语言。我后来发现,气味和音乐和时装和艺术一样,都是最能让人瞬间“身临其境”的东西。它超越了理性,也不需要翻译。你只要闻到,就能被带进某个情绪。这种共感其实比食物更直接。因为食物是味觉的,而气味,是记忆的。它能让你回到一个时间、一个人,或一段未说出口的感情里。
你为时装设计师XU ZHI创作的香气作品,有一种“安静的力量”。你认为香气能帮助人找到内在秩序吗?
我觉得是可以的。茶、香乃至食物的气息,都有“引导”的功能。它们不是去刺激,而是使人慢慢地——从“在外场”的状态转而到“临境”的情绪。当我做茶食搭配时,我会让味觉和气息之间产生呼应,而不是互相压制。比如,当茶是轻盈的、空灵的,我就会在茶点的口感搭配上做得更克制,甚至让味道有一点“留白”。这种留白,就是秩序的体现。它让人能在“少”的空间里,体会“多”的层次。
“气味”与“气韵”之间有什么关系?它能否被翻译成嗅觉、触觉甚至视觉语言?
“气味和气韵”是阴和阳,气味像是蜡烛燃烧的烛焰的光和色,气韵是周围化开的光晕和烛焰随气息跳动的韵律组成的流动的画面。 我一直相信,“气韵”是可以被转化的。我学的是设计,后来做时装、做餐饮,其实都在练习如何让感官互相“传话”。做菜时会潜移默化地用设计方式思考:如何加减、如何编辑、如何让节奏可被感知。气韵的产生会有有高有低,有留有放。有时候是轻重变化,有时候是质感的起伏。我想表达的,不是“某种味道”,而是一种呼吸感。
你觉得感官之间的边界在哪里?尤其在饮食、设计、气味的文化实践中,这条边界是否已经消融?
我觉得边界其实是人为的。我们习惯把“设计”、“料理”、“香气”分开谈,是因为它们在不同的行业系统里。但对我来说,它们的思维逻辑是一致的——都在讲“体验的节奏”。我最早做时装,后来做菜,那时我发现自己追求的还是一种“结构感”。只是从布料的剪裁,变成了味觉的层叠。但越往后,我越想“减法”。不再追求复杂的技法或夸张的层次,而是去掉多余,让气息自己显现。当空间足够清澈,气就能流动——感官的边界也就自然消融。
许多事物都需要等待——发酵、泡茶、香气的沉淀。你如何理解“气息的成熟”?
“气息的成熟”是一种从复杂走向简单的过程。好比我们以食物发酵为例,任何一个发酵过程都是向死亡向腐败而生,人为创造的条件是做一个定向的路径,微生物被选择的定向发展,我们判断这个气息的成熟是去判断这个平衡的点。中庸也是一种判断。就好比一开始我开餐厅的时候喜欢堆叠味道——甜的、酸的、咸的,让它们彼此碰撞。那时候觉得越丰富越好。但后来我发现,真正的成熟,是懂得克制。
茶是最好的老师。它教我等待,也教我如何倾听。真正好的气息是不会喧哗的,它总是留在空白里,留在呼吸之间。比如,有的茶刚泡出来味道很浅,但过几分钟会慢慢“打开”;有的香气在空气中停留一阵,会变得更温柔。这种变化是时间让它完成的。那么成熟,或许也不是让气息更浓,而是让它更有分寸。那种“淡”的气息,反而最能“听”到掷地有声的细节。

周义对气味有深厚的感知力,作为时尚编辑与译者,Edmund的工作高度依赖视觉, 但他关注的对象Galliano、Margiela、Rick Owens都带有浓烈的“气味想象”与“材质嗅觉”,这可作为他理解时尚的起点。这次,我们让他谈气与味如何塑造他对世界的认知。
你觉得嗅觉是更偏“记忆”还是“直觉”的感官?
就我自己而言,我是一个直觉型的人。很多时候我会凭气味来判断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感。比如初次见面的人,我会下意识靠近一点去“闻”他。如果那个“气味”让我觉得舒服,我会想继续靠近;如果让我不太舒服,我可能就会自然地保持距离。那种感觉,多半不是香水的问题,而是他“本身”散发的气味。我一直认为香水更像是一种装饰或伪装,是身体语言的一部分。但真正让我决定远近的,是那种自然散发出的味道。后来回想起来,这种直觉的判断几乎都是准确的。
嗅觉对我来说不仅是“直觉”,也有记忆的一部分。比如我到现在都能记得外婆做饭的味道——粉蒸肉、熏鹅的香气。那些香味其实早就超越了味觉,它们更像是时间的气息,封存在记忆深处。
时尚的“视觉语言”是否也带有嗅觉和触觉的延伸?
我觉得是的。很多品牌在香水的表达里,其实是在用气味补充视觉或触觉的感受。比如Helmut Lang的亚麻香水,它的清冷质地感很接近织物的触感;Bottega Veneta早期在Tomas Maier时期的香水,也在通过香气和瓶身设计还原或加强皮革、羊绒的触感。对我来说,这些香气不只是气味,更是一种掷地有声的语言。它们让嗅觉成为了视觉与触觉之间的桥梁。
从Galliano到Margiela,再到Rick Owens,他们的风格与世界观都截然不同。你翻译过这些设计师的相关书籍,在你看来,他们各自的“感官温度”是什么?
Galliano的世界是戏剧与浪漫的,是一种艳阳高照的热烈;Margiela早期的冷静与解构,他的气息是冷的,但不是冰冷,是大概二十二三度那样的秋日凉感;Rick Owens呈现出的阴郁与力量则是低温的,甚至带着一点阴冷感——像欧洲地铁里那种潮湿、封闭、略带金属味甚至轻微尿骚味的空气。
这些时装设计中体现“温度”并不只是视觉印象,而是在看过走秀、穿过时装、做过访谈之后形成的记忆。当我翻译与这些设计师有关的书籍时,我甚至会想象时装在传递出怎样的气味特质。这种感官联动的方式会让我在理解设计师作品时拥有新的视角与思路。
在时尚与美食中,都追求一种“辨识度”。对你来说,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官体验?
我觉得“辨识度”就是一种清晰明确的表达。它既来自原料,也来自比例和平衡。比如好的茶或酒,会有自己的“呼吸方式”。比如我最近在喝的一款正山小种,它带着淡淡的梅子香气,我会反复调整水温、冲泡时间、添加茶量,感受其中在气与味之间的变化 ,就像调香师一样调整原料的比例。
而在喝Aperol Spritz时,我们可以在酒体里感受到橙皮的苦与果汁的甜,这种在品味中体会到风味,让我想起那些柑橘调香水。它们都在用气味建立一种阳光明媚闲散惬意的午后风景。这种在品味时建立的辨识度更多的是“感受”——它让你瞬间识别出,那就是“它”。
当一个人能真正记住一种气味时,他其实在记住什么?
我想,是气味里藏着的情感——一段时间、一个人、一种心境。气味是记忆的媒介,我们真正记住的,其实是与气息相关的、当时当下的感受。就像我说的外婆的熏鹅,那股味道让我记住的不是鹅肉,而是那个厨房、那个下午的阳光,还有她在那里的样子。
编辑 CRYSTAL LI
撰文 王紫
视觉创意 OLIVER YEUNG VOIA STUDIO
修图 CC
微信编辑 李贝妮
微信设计 mona





 © 2025 现代传播 Modern Media Co,Ltd.
© 2025 现代传播 Modern Media Co,Lt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