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Weekly
2025年是里尔克诞辰150周年,2026年则是他去世100周年,最近在他的祖国捷克、奥地利(他在布拉格出生时,该地属于奥匈帝国)和语言母国德国,都有很多纪念活动和出版。
这种热闹,明显是有违里尔克的“寂寞”至上理念的,他早在三十多岁《写给青年诗人的十封信》里就强调寂寞的必要、唯有忠于寂寞才能认清命运、进入真正的诗与创造中。虽然他一生都在努力抵抗爱情、名声甚至生活本身对这种寂寞的破坏。
 △1913年,里尔克在黑森林里波尔德绍公园的一张长椅上。
△1913年,里尔克在黑森林里波尔德绍公园的一张长椅上。
里尔克在他为纪念波拉·蓓克(Paula Becker)——他的一个无法协调母爱和艺术创作的画家女友(这样的女友不少)——所作的《安魂曲》的结尾写道:“因为,生活和作品之间,历来存在着某种敌意。”这句诗,因为北岛在2011年中国香港国际诗歌之夜的引用,现在广为人知。
但这种敌意,其实更多地存在于里尔克的内心,一如他的同代布拉格人卡夫卡,里尔克的半生也纠缠于接受幸福爱情与像苦行僧一样献身写作这两者的矛盾撕扯,而他和卡夫卡不同的是,他的艳遇更多,且多数是艺术家或者贵妇,走马灯一般流转,然后被他以写作追求孤独而放弃的芸芸女子中,唯一例外的是比他大十五岁的奇女子莎乐美(她也是尼采追求过的,并曾任弗洛伊德助手的,可以说上个世纪初最伟大的三个灵魂都在她身侧交汇)。
我大概十八九岁开始阅读里尔克的诗和传记,当然也记得莎乐美这一段。最近重读三十年前读过的霍尔特胡森版本《里尔克传》,发现弗洛伊德曾经把这段感情当作俄狄浦斯情结(恋母弑父)的典型在精神分析大会付诸研究,这让人哭笑不得——也能看出即使是两个领域的顶峰,也是不能理解彼此的。
 △2016年德国传记片《恋上哲学家》中的里尔克剧照,背影为莎乐美。
△2016年德国传记片《恋上哲学家》中的里尔克剧照,背影为莎乐美。
按《里尔克传》里所述,里尔克早年跟一个浮躁功利的文学小青年差不多,是什么迫使他最终做出这么大的蜕变呢?后天原因主要还是前述他内心强烈的孤独感——或是对孤独感的渴求,以及他对万物敏锐的神秘主义思察和阐释,这两点令他不断从凡俗中抽离出来,企及更高的起点。而他身边的女性﹑贵族的庄园城堡以及他不断寻觅的“第二故土”都不过是他一时凭借的小小附着点,好让他的思与诗更浩大地爆发。
经历了俄国与巴黎﹑莎乐美与罗丹这两个“第二故土”和两个引领者的影响后,里尔克更一举跃到了成熟。俄罗斯广渺的沉重与苦难﹑东正教的神秘,应和了里尔克对存在与痛苦的思索。罗丹和塞尚的工作态度令里尔克在艺术形式上更像一个仅为艺术而生的圣徒一样磨炼自己,这是后来更高耸的飞跃的必经之途。《时祷集》是心灵上的锻炼;《新诗集》则是技艺上的修习,物的伟大凝聚;再加上《布里格随笔》中所作的自我责问﹑反思——他已为未来向巅峰的攀越做好了准备,然后就是十年的沉默。
最后来到里尔克的“奇迹之年”:1922年的2月,创造之神一下子完全占据了他的心灵,20世纪最伟大的诗歌出现了,在那不可思议的巅峰,里尔克的思与诗已浑然一体,甚至超越了诗人本身的能力,写出《杜伊诺哀歌》与《献给俄尔甫斯的十四行诗》之后,他已进入豁然开朗之境。这时作不作诗对他而言已经没有意义了,因为他已归属于他本真的存在的神恩之中。——也许后期的里尔克更应被当作一个思想者,而不只是一个诗人来看待,所以我们不应单纯用诗的尺度去衡量他的诗,并以此来指责他的形而上与过度的抽象。
顺便重读了茨维坦·托多罗夫的专著《走向绝对:王尔德、里尔克和茨维塔耶娃》,发现里尔克还有两个特别的情人和文学艺术史有特殊的联系。里面一笔带过里尔克一度有个犹太情人叫卡莱尔·戈尔(Claire Goll)——我看这名字很熟悉,一查竟然就是伊凡·戈尔(Yvan Goll)的妻子——就是日后污蔑保罗·策兰抄袭伊凡·戈尔,把策兰逼到精神崩溃的人。竟然,这就是策兰和里尔克的现实联系,虽然两人的诗在德语现代诗中早已组成一个谱系(存在主义或哲学性诗人)的两端。
 △1910年,里尔克与妻子克拉拉·韦斯特霍夫。
△1910年,里尔克与妻子克拉拉·韦斯特霍夫。
另外,里尔克的最后一个情人叫巴拉丁·克洛索夫斯卡(Baladine Klossowska),她是一个画家,也是日后更著名的法国画家巴尔丢斯(Balthus)的妈妈,里尔克还帮她照顾过年少的巴尔丢斯……他们合作出版了后者的第一本画册《Mitsou》,巴尔丢斯绘画猫主题漫画四十幅,里尔克作序——我发现我早在第一次去巴黎的时候就在巴黎买了这本金黄色的精装书,但今天才知道背后的故事,因为我只看了封面的Rilke大字,以为是里尔克的作品配上插图而已。
巴尔丢斯热衷于绘画未成年少女的性暗示,虽然他狡辩是为了呈现这种性欲之恶。这可看不出里尔克的影响,里尔克也重视性,但他更强调成熟的性、性的升华,以下这段他借他人之名虚拟的书信更能说明他的态度:“为什么使我们的性无家可归,而不是将我们主管的庆典移向那里? 好吧,我可以同意,这不属于我们主管,我们无力负责统辖这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欢乐。但是我们为什么不能从这处出发属于神呢?”(1922《青年工人的信》)
只是最后他那痛苦的病与死令人难以接受,仿佛也属于宿命的一步,是最后的考验。死于玫瑰刺所激发的白血病恶化,虽然痛苦,但却纯粹﹑独特(里尔克在《时祷集》和此后作品中都多次提出“独特的死”这一概念),向我们暗示了无尽的隐义。其墓志铭仿佛谶文:“哦,玫瑰,纯粹的矛盾,幸哉/在此层层花瓣下无人安眠。”——这也回应了那种“敌意”,花瓣代表着爱神的眼帘,急于安抚人生,而诗人最终从那矛盾中清醒过来,以死亡达至了超越。
iWeekly+
《鸣响的杯子》
作者:Donald Prater
出版社: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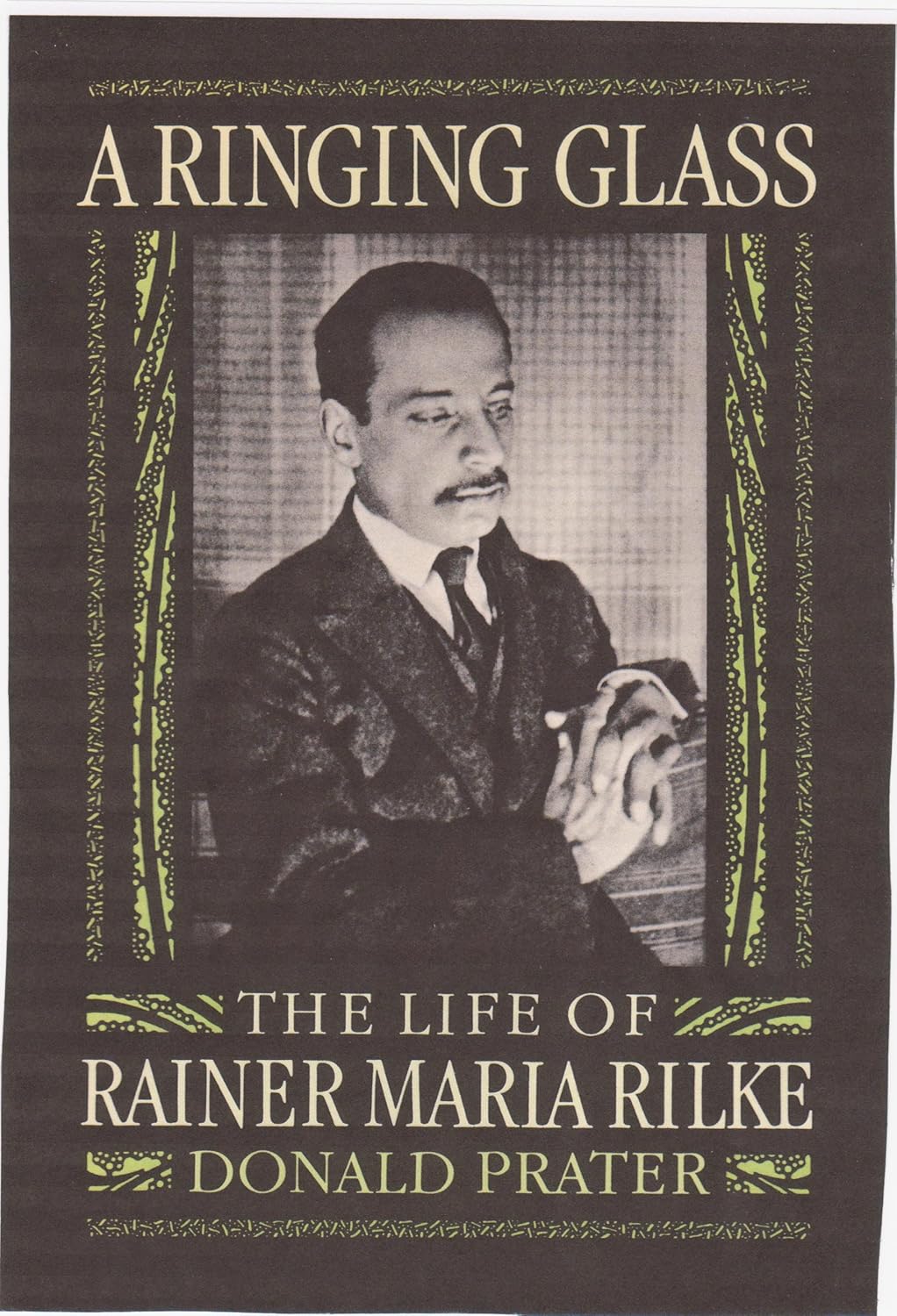
本书书名“鸣响的杯子”取自里尔克的十四行诗,象征着他将生命体验破碎重铸为艺术的创作哲学。全书以里尔克的生平为主线,讲述了他的漂泊生活:从出生地布拉格出发,途经德国、俄罗斯、西班牙、意大利、法国,最终抵达瑞士。其间,他曾前往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拜访托尔斯泰,也曾短暂担任罗丹的秘书,并且是罗曼·罗兰和帕斯捷尔纳克等人的朋友。他还有过多段恋爱关系。然而,里尔克仍然全身心地投入到自己的艺术创作中,并始终坚定不移地追寻其创作所需的孤独状态。普拉特引用里尔克写给友人的信件,揭示出他对这种矛盾的抉择:“最重要的是,你要问问自己,我必须写作吗?深入剖析自己以寻求一个深刻的答案。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就按照这个必要性来构建你的生活。”
《与里尔克同行》
作者:Stephanie Dowrick
出版社:Allen & Unwi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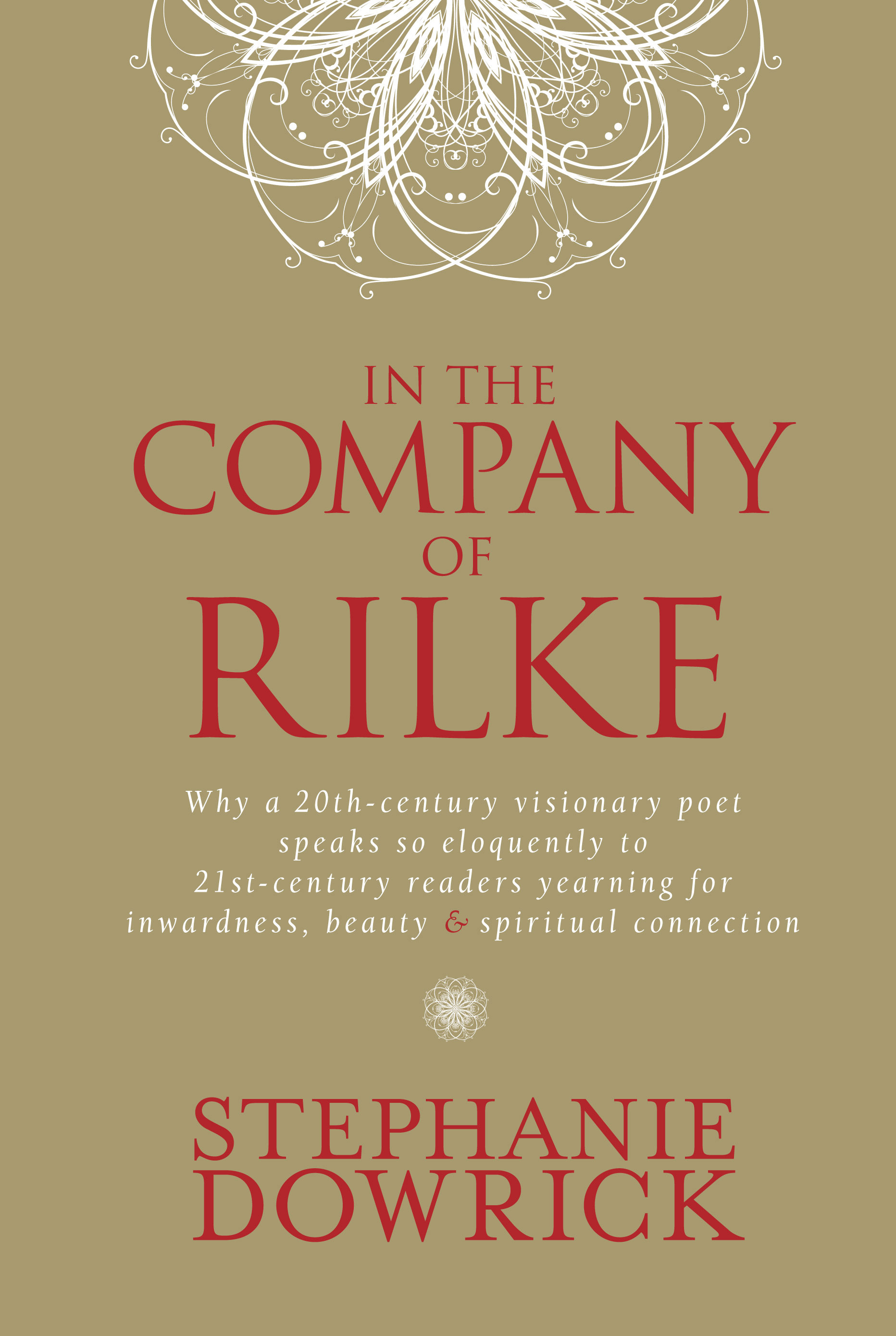
里尔克是二十世纪文学巨匠,如今正愈发成为我们这个时代富有远见卓识的声音,他不仅才华横溢,更以对“最深奥之事”的无畏态度吸引着当代读者,在自身的矛盾与摇摆不定之中,为读者深刻揭示着人类存在的复杂之美。而在本书中,里尔克研究学者斯蒂芬妮·道里克引领读者通过里尔克的诗歌走进他那超凡脱俗且美轮美奂的精神世界——那是一个问题比答案更重要,诗人既可以直面上帝,同时也能质疑上帝的世界。这也是首次有传记作家从精神层面深入研究里尔克。道里克指出,里尔克最伟大的天赋在于,他向我们展示了生命如何不可避免地围绕着一个深奥的谜团展开,而我们能够自由地敞开心扉去面对它。
内容来自周末画报
撰文:廖伟棠
编辑:北北
图片:视觉中国
iWeekly独家稿件,未经许可,请勿转载





 © 2025 现代传播 Modern Media Co,Ltd.
© 2025 现代传播 Modern Media Co,Lt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