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流人》系列的原作者米克·赫伦也没有预料到,电视改编版一季接一季地大受欢迎,中文翻译版图书也紧随其后。整个系列的名字用了《流人》,因此第一本为了加以区分只能译成《驽马》(Slow Horses),不知究竟的读者会困惑一下子,那么这个书系的鼎鼎大名“流人”又是译自英文的哪个词呢?
“流人”这个词,古已有之,《庄子·徐无鬼》里头有一句,“子不闻夫越之流人乎?去国数日,见其所知而喜”,这里的流人,指的是因犯了罪而遭流放的人。但在现代汉语里,流人一词的使用频率低得很,迹近消亡,直到被这出英剧激活并成了热词。不用困惑,流人就是Slow Horses的意译,Slow Horses的谐音Slough House(斯劳屋)就是书中、也是剧中这帮“废柴特工”被降职发配到的“冷宫”部门,要说是失意间谍、失宠员工的收容站也蛮合适。用流人来指代这些个被军情五处流放的边缘人,形象生动,贴切准确。同时,这个译法的妙处还在于,流人又跟牛人形成对照,高下立现——咱别故意折磨某些地界的朋友牛流不分的舌头就好。
《流人》的调调让人入坑(也算扣人心弦),虽是披着个谍战剧的外衣,却不靠或不大靠各种案情逆转与特工飒爽,甚至可以说,这些类型剧的既定趣味绝不是它的卖点。《流人》相当地“反007”、消解与祛魅,在大范围的观众和读者中间形成强烈共鸣,不仅能获得专业认可,也触动了大众甚至算是破圈,这其中蕴含的底层逻辑,也许有些超越剧集和娱乐的意义,值得多想上一想。
在我看来,很让大家代入的,也是尤其被其寓意打动的,莫过于军情五处主流快车道上的牛人与斯劳屋这帮前途黯淡的流人之间的鲜明反差,伴随着剧情层层演进,焦点问题逐集凸现——(至少是)在这个剧中,为什么流人比牛人更能得到我们的喜爱与追随,为什么流人而非牛人成了特殊难题的解法、复杂正义的脊梁,让我们同气相求,惺惺相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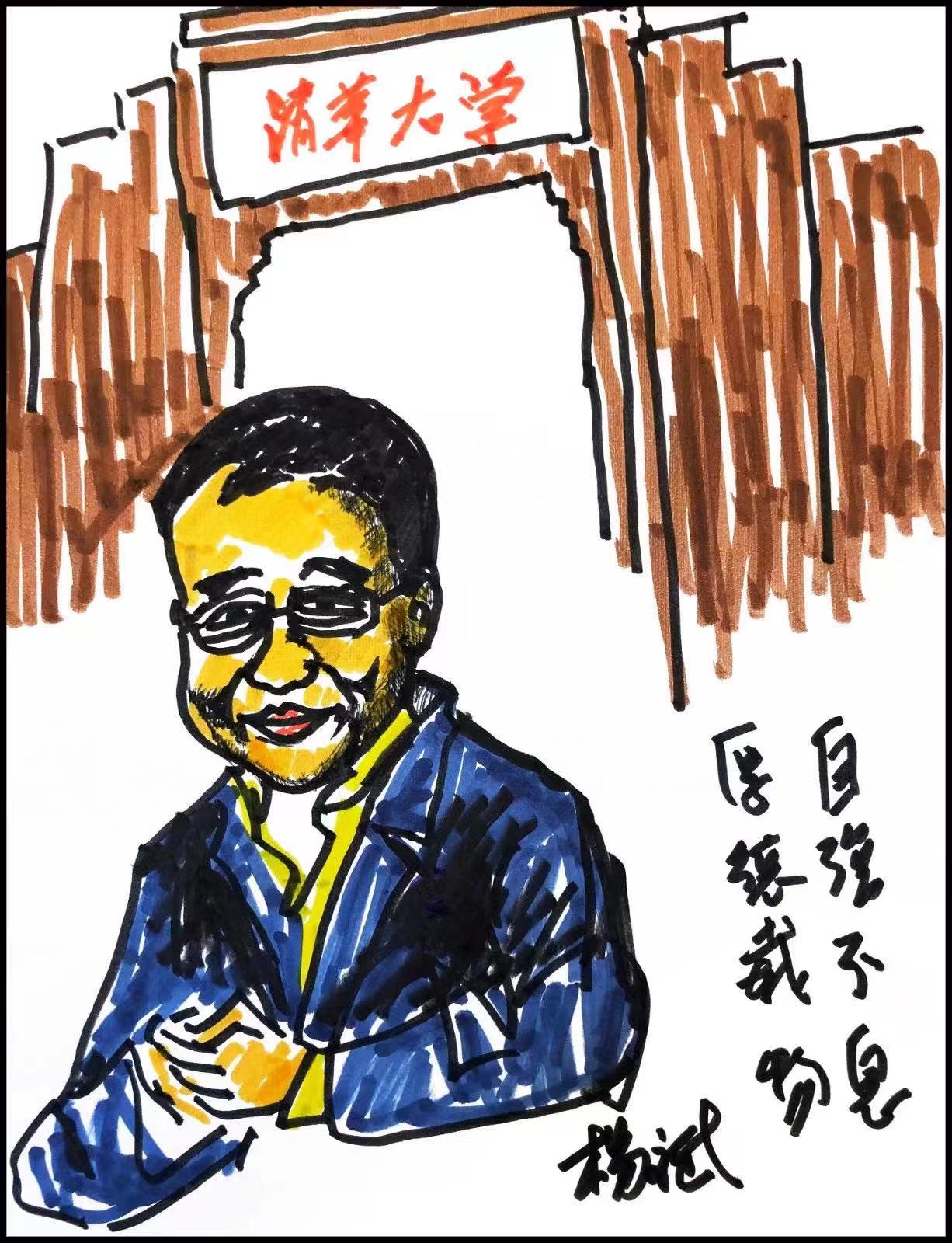 杨斌博士,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领导力研究中心主任,可持续社会价值研究院院长; 开发并主讲清华大学《批判性思维与道德推理》、《领导与团队》等精品课程; 著有《企业猝死》、合著有《战略节奏》《在明明德》,译有《变革正道》《要领》《教导》《沉静领导》等。
杨斌博士,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领导力研究中心主任,可持续社会价值研究院院长; 开发并主讲清华大学《批判性思维与道德推理》、《领导与团队》等精品课程; 著有《企业猝死》、合著有《战略节奏》《在明明德》,译有《变革正道》《要领》《教导》《沉静领导》等。
形式上,军情五处总部“公园”与流人所蜷缩的斯劳屋面貌迥异——总部代表着光鲜、高效、规范和权力源,而斯劳屋则象征着破败、低效、无序和边缘化。
总部的野心昭彰,照章办事,派系山头,专业骨干的机器化、零件感;为了维护体制的运转,人性可以压抑掉,个体可以牺牲掉,决策失误自然会被掩饰掉。而斯劳屋的挣扎求索,不拘一格,受迫而拧成一股绳,外表“失败”内心不同人生事故造就的破碎灵魂,各有个性、各擅胜场;在这个被遗忘的角落相遇,弃子们相互碰撞,也彼此温暖。都有各种不完美,却亦有难得的倔强和担当,和不跪的模样。
不用担心剧透,这不涉及剧情。《流人》涌动着的对体制(institution)的反省反讽,对牛人受制于体制而不抵因边缘化而获生机的流人,让很多观众和读者(实话说,很多先看剧后读书的朋友在捧读时,脑子里自动浮现的都是剧里的形象)全面唤醒了诸多关于自己和自己公司/单位经历过的种种记忆。而我呢,也许并不算奇怪地,想起了绝对堪称“管理老戏骨”的明茨伯格教授,他的思想和表达风格,跟流人的老大杰克逊·兰姆酷似;阴阳怪气、自嘲与讽刺、嘴仗与毒舌,这些《流人》书评里高频出现的词,也还挺合适他。
之所以想到明茨伯格,是因为我觉得若要总结“流人出奇”之道的话,也许他那些把人“组织起来”(organizing,他喜欢用动名词除了强调其动态性之外,也是与各类正式组织区分)的一针见血的冷观察、冷思考,能从组织方面提供给我们不少启发。
明茨伯格在他颇为自得的《卓有成效的组织》一书中,对现实中程序化机器型组织——剧中总部“公园”算是个典型——的长短处看得很透辟,“我们为什么要改变一个程序化机器型组织,让它做它不应该做的事情,而不是让它在自己的强项上提升呢?它的强项是效率,而不是创新(应变)”,在简单且稳定的环境中,程序化机器型组织大有用武之地;而遇到变局和谜团,就会在大费周章中原地踏步。虽然不是典型的专家聚合型组织,但是总部公园这帮专业间谍队伍在高度抵制各种外部变化的保守行为中体现的,正是明茨伯格所料到的在专家们遭受“外行指挥”“外人插手”(如剧中的政府部长高官所为)可能会产生的后果,“当外部影响者以错误的方式管理专家聚合型组织时,就会导致优秀的专业人士变得非常可怕”。流人则呈现出项目先锋型组织的那种含糊不确定性,在斯劳屋里,“权力会分散到任何能处理当下情况的人手上”,项目先锋型组织的不确定性、探索性、灵活性,是通过先行动而后调整来实现的,常常变通规则而非追求效率至上,因为规范和效率会扼杀他们的应变创造力。
当然是戏是剧,而不是现实,但还是要问为什么流人能合乎情理地表现得如剧中那样的非凡、意外、杰出——有趣的是,exceptional这个词本身就有例外和杰出两种义项——明茨伯格也许会回答说,因为任务的设定使然,要注意到“项目先锋型组织不太擅长做普通的事情,却很喜欢和擅长做一些非同一般的事情”。那又为什么(在剧中)总是会发生牛人折戟、总部蒙羞的后果呢?明茨伯格在导演版的音轨里会说,“一个组织不能又给它的员工戴上眼罩,同时却期望他们具有环顾四周的视野。”
看似乌合众实则十足变形虫的流人,在剧中的那些铤而走险和歪打正着的行为,一定不会发生在程序化机器型很强的总部牛人身上。否则,牛,就会被流。与其说狗屎运总是不断眷顾这些废柴,仿佛偏得逆袭之爽,倒不如说,是因为越来越多的(不止是剧中的,也包括生活中的)任务本身所具有的不规则、反常识、灰色地带等特征,需要创新多过效率,需要冒险多过规矩,需要流气多过牛气,才有不俗的创造力,才解决不凡的难题。而在大多数晴间多云的平常日子里,流人就是写文书干行政盯闲梢翻垃圾壁上观混工夫而已。
流人之道,除了在组织方式上暗合着某种摆脱规模优势和运营效率后的组织敏捷与创造释放,可能还有另一个重要因素——“边域”优势。
物种形成,又称为种化,是演化的一个重要过程,指的是生物分类上的物种诞生。种群内部彼此连通,基因交流,内部呈现高度一致性,新的突变很难在这个板结的基因网络中插足发展,即使面对环境压力,也很难有显著的整体演化——创新与变革鲜少发生。恩斯特·迈尔提出了物种打破自锁的几种可能,其中一种就借助边域。
何谓“边域”?一个小种群由于某种(各种)原因和原来的大种群隔离了,母种群基因对小种群的连通被切断、影响被阻隔;隔离在边域时,小族群的基因经历剧烈变化——也是各种原因(新环境、新趋势、新驱动,等等)——向外圈生态位扩张,旧基因让位于新突变、新演进;当小种群再跟大种群相遇时,已经形成了不同物种。这就是边域种化理论。恩斯特·迈尔发现,多数被隔离的小种群都会走向灭绝,而少数的成功者则可能会变成新物种,适配新的生态位。至于有的新物种在地理隔绝结束后,有缘与当年的母物种正面交锋,居然能很快就替代并灭绝掉了母物种——古生物学家以此来解释“化石断层之谜”就成了生物演化的“间断平衡论”,暂且搁下不表。
进一步思考,边域给了流人什么特别的优势?再跳跃一步,那是否会不可避免地演化形成新物种?
“少人关心少人问”,意味着边域的管理和规范远较中心地带松弛,在企业的边域部门,天马行空、离经叛道的子弹有机会能再多飞好一段时间,不那么功利(功利也没用)的行为动机可能会从理念和兴趣出发,引领创新方向,激活创造动力。边域往往也汇拢了不同背景、经验和专长的人才,这种多样性以及小群体之间更高效的互动有助于知识(尤其是隐性知识)的交流与融合,为创新和进化提供更丰富的素材。在边域探索新事物新做法,即使失败了也不会对整体组织和系统造成致命影响,由于风险承受度更高,往往探索和尝试的胆子和步子在边域会更大更无所顾忌。边域对环境更具适应性,没位子没架子没面子能够更加快速响应变化和需求。
我曾总结过创新型组织适宜的文化层面的“没”字诀——“没大没小”(更平等、去层级)、“没对没错”(重探索、无预设)、“没皮没脸”(轻面子,不怕输),而特别针对《流人》中的边域特征,原来的三条仍然都合适,另外还再增加上三条:“没牵没挂”(少牵绊,求洒脱)、“没遮没掩”(不婉转,更直率)、“没拘没束”(弱传统,尚自由)。这里所说的创新,不是延续性创新——我称之为线性改善,更多指的是颠覆性创新——质变与跃升,产生了新物种。
军情五处总部“采用的是封建的组织方式。这里有国王和贵族,也有封臣、士兵、侍从和农奴,他们之间有着层层的规约和特权(如汽车和司机),象征着地位高低,划定了不同等级之间的边界线。”而流人们却不同,他们“拒绝采用这种社会等级制度,每个人都应该把共同的目标内化于心。”这段话引自《区域优势:硅谷与128公路的文化和竞争》一书,比较的是美国东部大公司和硅谷初创企业的文化差别,在那个年代,硅谷正呈现出很强的边域特征,也演化出了科技创业家物种、科技投资家物种。
在硅谷与128公路的对比故事里,记得还有个以穿衣规则和喝汤姿势为代表的请客吃饭方式的比较。简单地说,东部在文化属性上更高阶也更正式,而处于边域的西部则文化门槛低且平实。东部请客的人会在意和挑剔你的衣着以及喝汤姿势(现在也不这么矫情了),边域则是随便穿、怎么咕噜咕噜干饭都随意。
边域跟总部、中心的隔离,有地理、管理、治理和心理几种不同的维度。“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天高皇帝远”,即使在视频通话如此便捷的今天,也能在心理上创造出某种边域感。公司在外国或外地派驻的经历,常常成为骨干快速成长的关键契机,因为人生地不熟的边域挑战确实有助于激发人的潜力,独挡一面的要求也更能淬火出主人翁精神、创造力和领导力。当然这种边域属于着意栽培的安排,与流人们的境遇大不相同。想起当年为了写微信创新案例,专门去采访过腾讯总部和广州微信团队,两地虽距离不远,但毕竟是两地,这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新物种的诞生。说“不可避免”肯定是期望过度,但增大了创新概率却不算太夸张。
流人出奇也好,边域创新也罢,共有的背景是大变局。《流人》剧中的大背景是冷战后“谁是敌人”与“间谍何为”的剧烈转向,而生物学史上的边域常举例说起地壳运动或地质周期的“纪元”巨变。这种大变局,“可能我们一生只会发生一次,但在历史上已经发生过很多次”。而正是重构秩序、再造范式的大变局中,流人出奇效,边域创新种。变局与下一次变局之间的漫漫岁月,流人和边域就只是静静默默地,无声又无息,间或一轮。
说到这里,自然会去触动我们借一步思考,如果流人与边域,对于创新与变革有这样的益处——流人出奇与边域创新,是否有必要专门去营造?是否有可能去人为创造出来流人与边域来呢?
西谚有云,“节食体验不到真正的饥荒”,增加组织中创新团队组成的异质性和群体结构的变形虫特征,在创新情境中滋养有“没大没小”、“没对没错”、“没皮没脸”、“没牵没挂”、“没遮没掩”、“没拘没束”风格的创新文化,也许都能有些效果;但斯劳屋里的那些个流人,却很难由组织以主动为之的方式去形成,顶多,去促进组织成员的“边域体验”,让新物种(产品、生意、文化)在边域中演化、突变,甚至变为组织下一波主流。正所谓——
流人出奇并非有心,边域创新或可着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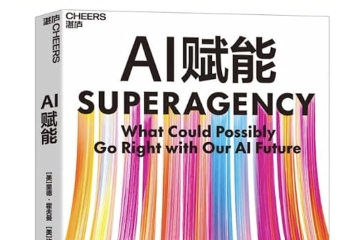

 © 2025 现代传播 Modern Media Co,Ltd.
© 2025 现代传播 Modern Media Co,Lt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