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柏林,创意不再只属于画布和舞台,而开始驱动代码与资本。这座城市已经跃升为德国乃至欧洲的创新创业中心,被称为“欧洲的硅谷”。
在德国柏林米特区的一处街角,曾矗立着一座充满涂鸦与铁雕的五层老楼,承载着整整一代人的理想与躁动。这就是塔赫勒斯艺术馆(Tacheles Art House)—20世纪末至千禧年初,柏林另类文化最具象征性的地标之一。建于1908年的它,原是商用大厦,二战后几度易主,陷入半荒废状态。柏林墙倒塌后,一群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音乐人、剧团和行为艺术家涌入,将这里变成了一个自由而狂野的创意乌托邦:白天是画廊与工作室,夜晚则变成地下乐队与实验剧场的狂欢圣地。
如今,这里已经不再响起吉他和鼓点。这座见证柏林文化复兴的“堡垒”在2012年被出售给一位纽约投资者,很快便被清空、封闭、翻新。昔日斑驳的墙面被刷成统一的灰白,取而代之的是高档公寓、写字楼、连锁超市、时尚店铺,还有一家瑞典摄影博物馆。
对于52岁的柏林土生土长的居民Oliver Putzbach来说,这栋楼的命运几乎象征着柏林整座城市的变化。曾几何时,柏林与欧洲其他首都格格不入。因为冷战分裂和代价高昂的统一进程,它贫穷、粗犷,却也充满生命力与创造力。现如今,这座城市正经历另一种转型。过去十年,柏林的经济增速持续跑赢德国整体表现。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去年柏林经济增长了0.8%,而德国整体经济已连续第二年萎缩。柏林人均经济产出也终于超越全国平均水平:54607欧元对比全国的50819欧元。
那些曾在涂鸦墙下起舞的年轻人,也许已经换上了创业者的身份。在柏林,创意不再只属于画布和舞台,而开始驱动代码与资本。这座城市已经跃升为德国乃至欧洲的创新创业中心,正被越来越多的人称为“欧洲的硅谷”。德国初创企业协会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4年柏林新成立498家初创公司,相当于每10万名居民中就有13.2家新企业诞生,在全国城市中排名第一,年创企数量超过慕尼黑。电商巨头Zalando、金融科技独角兽N-26等都选择在柏林扎根。
从无到有
土生土长的西柏林人Flip Sellin,曾赴伦敦研读工业设计,返乡后创办了著名设计事务所Coordination。他认为,柏林成为“创意之都”的最初契机,正是围墙倒塌带来的那股突如其来的自由感与表达欲。“大家太想庆祝了,急切地要释放压抑许久的情绪和想法。”Sellin说。
“我记得我在围墙倒塌的三年后去伦敦念书,每次假期回来,都会觉得柏林又变了模样—更自由、更欢乐。”他观察到,东柏林有许多居民突然离开,留下大量空置房屋。这些空间迅速被年轻人接管:有人开起酒吧,举办演出,夜夜狂欢。音乐响起,就需要宣传,这直接催生了街头海报、视觉艺术与设计文化的蓬勃发展。
“我认为,柏林的创意产业正是在那时起步的,最先兴起的是音乐与视觉艺术。”他说。
 德国首个国际化科技与创意社区 Factory Berlin
德国首个国际化科技与创意社区 Factory Berlin
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更像是打开了一道思想与创意的闸门。一切都需要重建,一切皆有可能。正因如此,柏林吸引了各类梦想家—从官员、艺术家、创业者到普通市民,无数人投身于这座“空白”的城市,赋予它新的意义。直到今天,提起柏林,很多人都会不假思索地说:“这是德国甚至全欧洲最自由开放的城市。”
从美国加州迁回柏林的国际建筑事务所GRAFT,正是看中了这座城市的自由气息与无限可能。GRAFT三位合伙建筑师无不赞叹柏林多元而充满张力的创意土壤。“这里永远有新面孔、新文化不断注入。”合伙人Putz说,“俄罗斯人来了,巴黎人来了,荷兰人也来了,在柏林相遇、碰撞出新的火花。这里就像夏天的巴黎,冬天的莫斯科,总在世界的目光中。”
“柏林是一座为25到35岁年轻人而存在的城市。”另一位合伙人Cook Berg补充道。“对初入社会的青年与刚起步的艺术家来说,这里简直是天堂。人们似乎都没有朝九晚五的工作,却整天泡在咖啡馆里,聊着聊着,就诞生了一个新点子。”
向新发力
在柏林市中心,一栋改建自旧啤酒厂的六层砖楼内,一片创新热土正悄然生长—Factory Berlin,德国首个国际化科技与创意社区,也是德国最受欢迎的初创空间之一。阳光透过大窗洒进开放式办公区,水泥墙上挂着现代灯饰与艺术家作品,一旁的露台飘出咖啡香,转角处便是柏林墙遗址。科技与历史、创新与艺术,在这里奇妙交汇。
创业数据平台Gründerszene统计显示,约19%的柏林创新企业选择在此落脚,包括Mozilla(火狐浏览器开发商)、SoundCloud等知名企业都曾在此起步。这里不仅设施齐全,氛围也充满硅谷式的自由与活力:午休室、滑板车、3D打印站应有尽有;员工或穿梭于苹果电脑前,或倚在沙发上看书,墙上甚至还挂着一把吉他。会议室以安迪·沃霍尔工作室常客的名字命名,彰显创意本色。许多独立的科技工作者,只要一个月交50欧元(约合55美元),就能在一处公共工作区内办公。
Factory的共同创始人Lukas Kampfmann称:“这更像是一家创业者的社交俱乐部。我们深受美国文化影响,从电影、音乐到时尚,柏林正成为欧洲的硅谷。”
而在柏林西部另一栋其貌不扬的大楼中,一家名为The Drivery的创新企业崭露头角。它是德国首个专注于移动出行领域的共享空间,致力于为初创公司打造合作与交流的孵化平台。整个空间占地近一万平方米,其中700平方米可容纳多达200个协作办公位,还有一个可举办500人活动的开放场地。初创企业在这里不仅能找到场地,还能获得水、电、咖啡、打印等一站式支持。
而且,The Drivery并不以盈利为目的。“我们追求的是收支平衡,把多余资金再投入到优秀的初创团队中。”创始人Timon Rupp表示,项目从一开始就完全依靠私人资金,没有接受国家或政府补贴。即便在初创阶段,入驻率就已高达70%,可见其在柏林创业生态中的受欢迎程度。
如今,来自整个欧洲的年轻科技人才正在涌入柏林。他们流连于咖啡馆、共享空间、改造后的苏联旧楼,为这座城市轻松开放的生活方式、较低的生活成本和多彩的夜生活所吸引。在欧洲,很难找到第二个如此“宜创”的城市。
27岁的程序员Martin Hellwagner就是其中一员。他于2014年初从奥地利搬到柏林,如今供职于音乐教学应用Uberchord,每周工作近60小时。“与传统大公司不同,在初创企业你真的能影响结果,你的声音会被听见。”他说。
目前,Factory在柏林与汉堡均设有园区,吸引了来自90多个国家的4500多名会员,汇聚150多家初创企业。到2023年,该平台已帮助企业筹集超过56亿欧元的创新基金。首席执行官Zino Sojka表示:“我们希望打造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协作网络,连接不同行业、不同阶段的创业者、投资人与创意者,孕育出欧洲下一代科技巨头。”
孵化“密码”
有别于传统的创新孵化器,柏林创新社区(Factory Berlin)以商业俱乐部的运营模式,构建了一个跨界融合、协同共生的创新生态系统。这里不仅是创业空间,更是一张联结创意、资本与人才的网络。
“我们不是简单的办公空间提供商,而是一个能够催化创新反应的实验场。”据项目经理Dinah Gay介绍,社区采用严格的会员筛选机制,为不同发展阶段的初创企业提供从灵活工位到专属办公室的梯度化空间解决方案,同时配备个性化的资源对接服务。
科技创业者Niels对此深有感触:“初创企业就像需要精心培育的幼苗,这里提供的不仅是物理空间,更是一个能够快速生长的创新微环境。”
真正让柏林创新社区在众多创业平台中脱颖而出的,是它那一整套围绕“赋能”展开的系统化支持机制。这里不仅是办公的空间,更像是一个高速运转的“创意引擎”。
 有别于传统的创新孵化器,柏林创新社区以“商业俱乐部”的模式运营
有别于传统的创新孵化器,柏林创新社区以“商业俱乐部”的模式运营
每年,这里上演超过400场专业活动。从干货满满的创业路演,到直面资本的投资者反馈会,再到思想碰撞的内容创作者论坛,为初创团队搭建起通向市场与资源的快速通道。这不仅帮助他们厘清商业化路径,也让他们在真实语境中遇见潜在合伙人,推动项目真正“落地生根”。
今年,创新社区还将携手德国知名人才组织,在汉堡发起一场别开生面的“人工智能马拉松”挑战赛:参赛者将在24小时内,基于企业提供的真实业务场景,现场提出AI解决方案—这不再是纸上谈兵,而是一次真正让技术“落地”的极限创意实战。
在这样充满协同与创造力的氛围中,一批具有潜力的初创企业迅速崛起。比如,成立于2017年的Vyking,正是在柏林园区内完成了从概念到产品的飞跃。这家聚焦科技与时尚交汇的公司,敏锐捕捉到行业的数字化浪潮,凭借增强现实(AR)、3D建模、计算机视觉与机器学习等前沿技术,开发出一套可无缝嵌入多平台的虚拟试衣解决方案,广泛应用于电商平台、移动端应用乃至实体零售门店。
不仅如此,Vyking还推出了为线下零售打造的“AR试衣镜”:消费者只需在店内进行一次数据匹配,便能在不同设备上随时预览服饰穿搭效果,线上线下体验浑然一体。截至目前,其系统的月均使用次数已超过1300万次,覆盖全球80余个平台、2万多件商品,并已与多家国际知名品牌建立合作关系,成长速度惊人。
而让像Vyking这样的创新公司不断迸发活力的,除了物理空间中的共享与互助,还有柏林创新社区搭建的全球线上协作网络。这个由来自90多个国家、超过5万名专家、工程师与创意人才组成的虚拟系统,为跨国、跨界、跨规模的资源交流提供了强大基础。
“在这个网络中,有想法的人可以迅速找到彼此,建立联结。而这些联结,往往就是灵感迸发、项目诞生的起点。”创新社区市场部项目经理Dinah Gay说,“这正是创新的本质。”
根据欧洲专利局近日发布的《2024年专利指数报告》,德国在2024年共提交专利申请约2.5万项,稳居全球第二。与此同时,安永会计师事务所在《2025年创业报告》中指出,德国初创企业在2024年共吸引投资逾70亿欧元,同比增长达17%,显示出强劲的发展势头与资本吸引力。
依然性感
如今,柏林企业的国际化,早已不再局限于从德国拓展到奥地利、瑞士这样的德语区国家,而是实实在在地走向亚洲、美洲乃至全球市场。走在街头,异国面孔随处可见,不同语言在咖啡馆、会议室、地铁车厢中交织响起,构成了这座城市全新的日常。
人才的国际流动与企业的全球化布局,也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强烈的联动效应。“我们观察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来自初创服务机构的Gary分享道,“很多企业一旦发展到一定规模,便会自然而然地寻求国际化扩张。这时,他们就急需具有国际背景的人才。这种需求反过来也推动了企业文化的演变。在过去,公司内部普遍使用德语,而现在,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将英语作为官方工作语言。”
Gary回忆说,几年前,柏林的国际人才还常常因为语言障碍、签证限制、文化差异等问题被迫离开;而今天,情况已然颠倒。“现在,如果不具备一定的英语能力,连本地的德国人也很难在科技创业领域找到一席之地。”
尽管柏林经济持续升温、创投资金不断涌入,但对本地居民Oliver Putzbach而言,这份“繁荣”却并不令人欣喜。
近年来,柏林的房租虽然仍低于慕尼黑、汉堡等德国一线城市,但住房平台ImmoScout24的数据显示,自2021年以来,柏林租金已累计上涨约32%,远高于全国平均涨幅20%。高涨的生活成本,让许多老居民感到“压力山大”。
不仅如此,柏林仍在追赶德国传统经济强市的步伐。2024年,这座首都的失业率为9.7%,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6%;而月均毛收入为4634欧元,也仍落后于慕尼黑、汉堡、斯图加特及法兰克福等城市。
尽管挑战重重,柏林的进化依旧令人瞩目。德国创新事务专家Gornig指出:“若将时间拨回20年前,柏林那时还只是一个以政府机构为主的城市。而今天,它已经逐渐成长为经济活力强劲的都市中心,这是非凡的进步。”
在一些老柏林人眼中,这座城市的“锋利与叛逆”似乎正在被资本和秩序所磨平,但对于新一代迁入者而言,柏林依旧是理想与自由的代名词。就像来自乌克兰的年轻人Egorchenko所说:“‘爱的大游行’(Love Parade)、‘狂舞星球(Rave the Planet)’……这些街头活动依然代表着柏林的开放、包容和创造力。”
他笑着补充:“也许有些角落不再性感,但整体而言,柏林依然性感、依然酷,依然令人惊艳。”
撰文— NiuNiu
编辑 — Ame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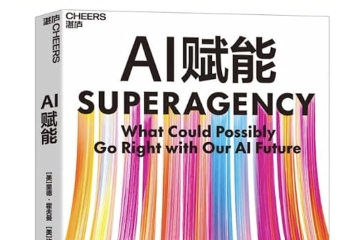

 © 2025 现代传播 Modern Media Co,Ltd.
© 2025 现代传播 Modern Media Co,Ltd.